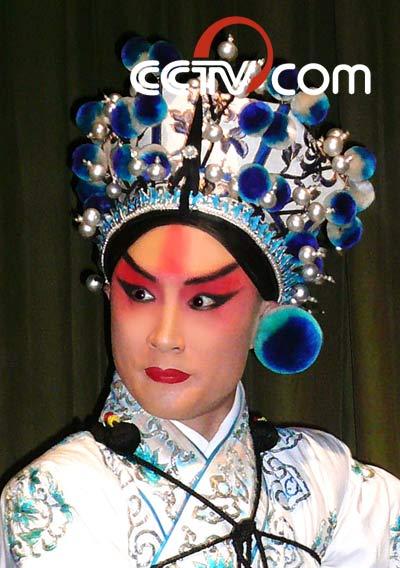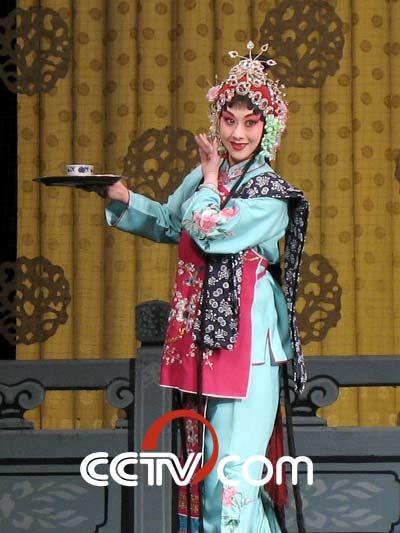开垦京剧学研究的处女地
——谈实验戏剧的探索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断升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突出代表的京剧艺术受到更大程度上的审视。如何传承传统剧目、推动新创剧目的问题,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京剧艺术工作者需要在实践中慎重地找出更好的出路,真正起到发展京剧的目的。
作为一个亲身参与艺术创作的实践者,我这些年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涉及京剧、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诸多领域。这些探索性的新剧创作,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在摸索中。本文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为切入点,结合探索实验工作中的具体体会,从创作者、实践者的角度谈对实验戏剧的研究心得,研讨实验的目的和意义,探寻实验戏剧的本质,与所有愿意对传统艺术进行思索,愿意从事京剧研究的艺术家们,一起分享实验戏剧创作中的成败得失,共同交流探讨京剧发展的未来,与艺术同仁共勉。
一、实验戏剧的探索在京剧学研究中的定位
京剧学研究可以包含对于京剧历史和京剧文学、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包括对于京剧创作的研究。在京剧创作研究中,可以分为整理、改编、移植、新编及探索实验等形式,其中探索实验戏剧不是完全以京剧舞台形式进行创作,而是运用京剧舞台创作法则及“四功五法”的表演元素组成新的表现手段,塑造人物,演绎故事,呈现出新的演剧模式,在传承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
二、实验戏剧在舞台表现形式上的特性
(一)在京剧法则中,以京剧元素进行新的舞台形式探索
实验戏剧并不演出完整的京剧剧目,而是继承传统的深厚底蕴,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京剧的创作法则、美学原则下,直接运用京剧的元素和技术手段进行创造,运用于演出中,开展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
(二)得意而忘言,赋魂不拘格
实验戏剧在形式上跳出京剧的基本模式,把京剧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表演体制、美学精神等赋予其他艺术形式,将京剧的魂魄植入其他艺术体内,使其血液里流淌着京剧的因子,充满京剧的韵律和气质,以一种无形渗透的方式体现京剧的精髓,传承戏曲的精神。
(三)反作用于传统京剧,拓展京剧的发展空间
以经历过实验戏剧探索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戏曲,反作用于京剧的传承,重新投入传统戏的排演,会将更新的思维观念注入戏曲本体中,把真正属于本质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更加细致地融入传统剧目的继承和再创造。摸索京剧的边缘,延伸京剧的前沿,拓展京剧的发展空间,为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三、实验戏剧在探索过程中所需的条件
(一)探索实验的意识
1、前瞻性的观念
以前瞻性的观念,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创造力,进行自觉性的创作,开展不同程度的创新。只有充分预见实验戏剧的远景,才能主动而不被动,自觉而非自发,从表面走向本质,有意识地开展创作,才能做得精致、精到,真正起到继承和发展的作用。
2、让历史与现代互动的灵感
在演出历史题材剧目,塑造历史人物时,需要在演剧形式上与现代人贴近,与现代观念互动,折射出现代生活,既传统又时尚,非常具有时代感。戏曲作为古老的艺术,需要发挥艺术灵感,从艺术结构、表演形式上开展研究思考,进行探索实验,达到与传统在本质上的契合,与观众内心的沟通与共鸣。
3、抵御外界压力的勇气
纵观京剧史,是几代京剧人不断进行不同程度创新的过程,很多大师都在不停地创作新剧,但改革发展的举措和创新剧目的推出,往往伴随着不同意见的声音和来自不同力量的抵制。实验戏剧的探索者应该摒弃躺在传统温床上的惰性,抛开厚古薄今的风气,树立抵御外界压力,开展创新实验的胆识和勇气。
(二)探索实验的能力
1、大量深厚的传统积累
开展新剧目的实验、创作,进行改革创新,必须建立在戏曲艺术深厚的传统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基础,才能进行新剧的创作,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没有基础的创作是盲目的、危险的。继承传统要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数量上,要继承丰富的优秀经典剧目,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质量上,演出剧目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只有精确继承、精彩演绎才能真正起到打基础的作用。所有的艺术家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传统基础的条件具备了、成熟了,才能创作新剧,进而进行探索和实验。
2、开阔的眼界
眼界开阔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与融合,在更高层次上使戏剧观得到升华,从世界戏剧的广度和高度重新审视中国戏曲,对戏曲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从而提高认识水平,促成艺术观念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在与其他艺术形式艺术家的合作过程中,对其他领域的艺术会获得更多的感性认识和了解,在艺术创作等方面形成更多的积累。想到是做到的前提,而做到更多才能想到更远,这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这种眼界有益于艺术上的创意,是实验戏剧创作的宝贵财富。
3、包容、化合、升华的功力
在创作中要有兼容并蓄的气度,吸收各类姊妹艺术的优秀成果。吸收之后并不是做简单意义上的加法,实行拼凑嫁接,而应经过提炼、升华,最终达到融合,了无痕迹,化于其中,化为己有。这不仅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更需要吐纳自如的造诣和“万物为我所用”的艺术功力。
四、京剧与其他艺术交流的几种表现形式
(一)不同艺术形式的碰撞
1、以京剧形式演绎外国故事
以京剧的艺术形式进行编创,即用京剧演外国故事。一种是套用原版剧情、人物和造型,采用京剧手段表演的“中国版”外国戏,如《美狄亚》、《奥赛罗》等。另一种是仅采用原版的故事梗概和剧情模式,将人物附会为中国古人,采用戏曲造型的“中国化”外国戏,如根据《李尔王》改编的《岐王梦》、根据《巴黎圣母院》改编的《大钟楼》等。
2、几种戏剧形式的同台合作
中外艺术形式在一起创作,舞台上不同的演员演出各自的剧种,一半京剧和一半外国剧拼盘成为一台戏,让外国观众看本国戏剧时也欣赏到中国戏曲的民族艺术形式,如京剧与日本歌舞伎合作演出的《龙王》等。
(二)与其他艺术的内在融合
京剧融入其他戏曲剧种或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等艺术形式,拓展新型的演剧方式,在融合中体现京剧的独特魅力。这种融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戏曲形式
利用传统戏曲元素,加进一些其他元素,依然是在戏曲的模式下演出新剧,如昆曲歌舞剧《贵妃东渡》、京剧交响诗剧《梅兰芳》等。
2、西方戏剧形式
游离于纯戏曲的创作手法和创作模式,不再以戏曲面貌出现,但大量运用了戏曲的表演精华,作为各种西方戏剧形式演出,如实验戏剧《巴凯》、实验歌剧《文姬·胡笳十八拍》等。
3、不同于已有戏剧的实验形式
以一种探索的,暂时难以界定的艺术形式演出,不属于任何一种已有的戏剧形式,更加边缘,如《诸神会》、《穆桂英》、《故事新编》等。
五、以三个剧目为例谈实验戏剧的创作实践
(一)《巴凯》——戏曲的程式性对古希腊悲剧戏剧舞蹈的演绎
实验话剧《巴凯》是1996年由美国纽约希腊话剧团与中国京剧院联合制作演出的,在欧洲戏剧家云集的纪念欧里庇得斯诞辰展演中,它从众多同一题材的戏剧作品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当时欧洲戏剧中心主席的赞誉:“这是我所看到的表现这一题材的最有震撼力的一出戏。”
中国戏曲和古希腊戏剧的对话与融合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探索,古希腊戏剧流传至今,有据可循的资料越来越少。用戏曲程式化的歌舞形式,对仅存于史书记载的古希腊悲剧中主演的表演和舞队的舞蹈进行重新演绎,极富挑战性。古希腊悲剧中原有歌舞表演,但没有达到高度程式化。戏曲的“表演程式,就是生活动作的规范化,是赋予表演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格式。例如关门、推窗、上马、登舟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许多程式动作各有一些特殊的名称,例如‘卧鱼’、‘吊毛’、‘抢背’等。”我在《巴凯》中大量运用了如“旋子”、“飞脚”、“串翻身”、“朝天蹬”等程式化身段,充分运用戏曲高超的程式技艺,发挥了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特殊表现力。
当狄奥尼索被士兵捆缚上台的时候,我借用了京剧程派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的“慢步量”,这样的出场台步意在以阴柔表现神的不可抗拒,并给人带来一种未知的神秘感。在表演过程中,我还采用了一系列的武打动作。狄奥尼索不加反抗地被捆绑到潘希斯面前受审时,我用一个360度的旋子,加上一串串翻身,来表现狄奥尼索身为神的威力,这是其它艺术门类的演员完成不了的,却是武戏演员的基本功。当剧情发展到狄奥尼索以公牛为自己的化身戏耍潘希斯时,我用手中的神杖耍了一套棍花,力求以戏曲特有的方式尽显狄奥尼索的戏耍之意。武功在剧中运用的极致,在于表现宫殿被法力倾覆时的一个硬卧鱼加一个腾空转身叉,尤其是后一个动作表现的就是大厦倒塌的场景,是以舞台的抽象写意表现生活实物的范例。
(二)《文姬·胡笳十八拍》
——戏曲的综合性对歌剧以唱为主的丰富
歌剧《文姬·胡笳十八拍》2001年由美国亚洲协会创作,在美国纽约演出多场,盛况空前,谢幕最多达到十三次,让观众在西方歌剧里充分领略了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在参加香港艺术节的演出中,得到香港各界好评。
歌剧重在声乐,是以演唱为主,其他表演形式为辅的戏剧形式。“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拥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的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我在歌剧《文姬·胡笳十八拍》中融入大量的戏曲综合性的演唱、念白、做功和武功,通过戏曲中不同行当和角色的表演,大大丰富了歌剧的表现手法,增强了歌剧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我在剧中兼演说书人、汉使、蔡邕、汉将四个角色。说书人是身穿长袍的形象,汉使是类似小生的中性行当,蔡邕是戴白髯口的老生,汉将是身怀武艺的花脸,还要串演左贤王手下的一个打手,是说书人临时演变的小丑。我实际上担当的是一个串场人的身份,通过不断变化角色,一个人完成全剧的起承转合。我在舞台创作中还担当了技术导演的工作,充分运用戏曲表演的创作法则,安排具体的舞台调度和人物动作,让西方歌剧演员在舞台上充满中国戏曲表演元素。
开场时,我随着音乐开始唱:“乱世起烽烟,群雄逐鹿中原……”,突然转身一变,用女性的动作,以文姬的口吻述说战乱的切肤之痛和远离故土的思乡之情。文姬在去北国的路上,我又转换为一个汉将,通过形体的表现、说话的声音转换场景,仅靠一个人就表现了左贤王带着文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行的场景。文姬在北国思念故土时的情景,我变成蔡邕,有一大段咏叹调,是对自己心爱的焦尾琴的赞美:“声如钟磬,圆润清纯……”,这段演唱基本是清板,用古琴伴奏,古典风格非常浓郁。
左贤王为了给文姬抢琴,兵发汉朝。他下去换铠甲时,我拿着一把大旗上场,设计了一套旗舞,表示出征。左贤王兵临城下,我扮一个小丑来报信。左贤王站出来了,我进去之后马上戴着一字胡,拿着宝剑,走台步出来,变成一个汉将前来迎战。对于开打的处理,导演不满足于仅是声音上的表现,而且希望通过肢体语汇,让观众从视觉上也有所理解,更能烘托音乐形象的塑造。两人在台上各站一边,只根据鼓声节奏的变换,面对观众表演出进攻、防御等各种动作,空对空地打,但让观众觉得双方是在对打。虽然没有武术的短兵相接,但开打的神态、动作的节奏都很强烈,而且运用了旋子360等很多高难度技巧,展示了腿功,营造的氛围是互相在打斗。这场戏的构思和开打的动作设计由我来完成,战争场面完全靠演员的唱、念、做、打来表现。因为我是戏曲演员,懂得发掘和运用戏曲的表现形式,不仅我自己这么做,也引导歌剧演员这么做。
左贤王抢到琴送给文姬后,他们有一段抒情的咏叹调,但导演觉得仅用唱不足以烘托他们美好情感的升华,我就通过虚拟表演渲染这种环境。我利用一个大圆月亮道具,双手托起从舞台的上场门起,走云步至下场门,循环舞动两次,用形体表演表现大草原的夜色,描画月亮缓缓升起又缓缓降落,周而复始的景象,也表现两人恩爱进而融合的场景。最后我又变成汉使,盘膝而坐,抚琴一首,唱了一段“仲尼思归,鹿鸣三章……”,希望通过词来打动文姬,劝其归汉。
(三)《弘一法师》——戏曲的虚拟性对话剧写实时空观的突破
实验话剧《弘一法师》2003年在首都剧场首演,在上海、北京等处都曾演出过,其中尤以上海反响最为热烈。戏剧理论家田本相著文说:“话剧学习中国戏曲的历史,可以说同话剧的历史一样长久。……在表演上直接把戏曲的身段、韵白化到话剧的表演之中,化到整体人物的塑造之中,《弘一法师》还是一个独创。设想,……不是有机运用了戏曲的优美的身段,以及十分具有表现力的韵白,还是话剧原来的对话和表演,是不可能如此深刻地表现弘一法师的精神历程和精神世界的。”
话剧采取分幕制,运用写实的时空结构,“把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采取以景分场的办法,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把戏剧矛盾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在同一场中,情节的延续时间要求使观众感到与实际演出时间大体一致,时间的跨越则在场与场的间歇中度过。这就是西方戏剧中自有‘三一律’以来的多年采用的基本结构形式。”但《弘一法师》是无场次不分幕的,“从他即将圆寂写起,着意刻画他的精神历程,而最后又以他的圆寂而更收缩。这种写法,需要眼光,需要一个开阔、超越、独到的视野。”这种时空不断自由转换写法决定了话剧的时空观无法完成该剧的舞台结构。“戏曲的虚拟性首先表现为对舞台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它有一种假定性,即和观众达成这样一个默契:把舞台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当作不固定的、自由的、流动的空间和时间。舞台是死的,但是在戏曲的演出中,说它是这里,它就是这里;说它是那里,它就是那里。……运用自由,富有弹性,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涵义,完全由剧作者和演员予以假定,观众也表示赞同和接受。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使戏曲把舞台的局限性巧妙地转化为艺术的广阔性,这就是戏曲的虚拟手法的集中表现。”我在《弘一法师》中采取戏曲的虚拟时空观,打破话剧的演剧形式,实现了时空自由转换,表达出了该剧独有的格调和韵味。
这部作品采取的是一种时空转换、跳进跳出的较为自由的方式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且带有极强的人生哲学感悟的色彩。我采取了一种杂糅的表现手段,将话剧的真实与戏曲的虚空、缥缈、抽象有机融合在一起,且尽量找寻剧本台词所需要的那种灵动的效果。
戏中戏是该剧的一个特色,在剧本谈到“教会我演戏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艺妓”时,紧随其后的就是一段戏中戏——昆曲《秋江》。为了将人物由戏里的现实引入戏中戏且不显得生硬,我以僧袍的宽大袖管代替水袖,以类似戏曲中耍水袖的表演顺利且自然的地完成了人物在两度空间内的跳跃。整场演出都是在不更换服装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演《山门》、《秋江》、《茶花女》片段时,所着的都是僧袍,目的是在服装和化装都不改变的前提下,在瞬间实现时空的转化。
六、实验戏剧的意义
(一)更新对于继承传统的认识理念
戏曲艺术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要赋予其生命力。狭隘的单纯固守继承不能很好地防止传统的流失,更难以发展传统。应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承,需要人的创造力不断介入,就要有创造性的技术才有生命力,在发展中、改革中、创作中继承,才能延续发展下去。要在技术结构上进行一些新的再创作,甚至进行一些整理和改编,进行一种互动。在发展、创造中的积极继承、动态继承才是最好的继承。
从继承的角度看,走到边缘,走到尖端以后,才知道应该继承的并不是表面,而是本质的部分东西。继承并不仅限于学演某一个技术、某一个剧目,摈弃真正的思想本质才是最致命的。在戏剧创作中要主动向最高一层、最边缘勘探,通过实验戏剧的探索,在实验中反馈传承,为后人提供平台,让后继者进行新的传承,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起到一种真正的带动和推动。
(二)为排演新剧提供新的思路
排演新剧应该大胆地探索其边缘,敢于冲出戏曲本身固有的模式。大胆与各剧种及其他艺术形式互动,对戏曲本体进行实验。这种实验本身可能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精神、意识和观念领域起了一个启蒙和带动的作用。在实验室中可以失败,但必须做这个实验,为第二批的实验者提供丰富的经验,或让其看到实验的过程,让他们的实验有更高的起点,更加准确地进行创作。这种作用是最重要,其意义远远大于某一出戏本身的成败。
实验戏剧的目的在于反思戏曲本身,探索艺术的本质,寻找和拓展戏曲元素在舞台呈现上更多的可能性,丰富戏曲的表现功能。达到思想观念上一个新的高度后,反馈到戏曲上进行重新审视,会对戏曲有更新的认识,带动人们运用新思路调动戏曲元素进行新戏创作。
(三)挑战创作底线,拓展艺术空间
戏曲在与其他的艺术碰撞合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创作的底线。这种创作并不完全以戏曲的规律来进行,需要进行新的挑战。实验中应该超越一般实践,打破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冲击艺术的底线。作为传统艺术,在做实验时需要挑战本身的艺术形式、创作法则、创作观念和审美观念,冲破自己的最底线。每冲破一道防线,艺术的空间就拓展一层,但冲过去并不代表永远在底线徘徊,是证明一种可能性,探究可能性的最大化,为自己的艺术提供在已证明的底线以内更大的回旋余地。需要在传承传统艺术本质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更远的探索。
(四)推行“送去主义”,传播民族文化
戏曲不仅要有“拿来主义”的思想,不断地吸取其他艺术的优点来丰富自己,还要有“送去主义”的态度,敢于延伸自己的影响力,在以与各类艺术形式的交流和融合中推广自己的艺术,渗透自己的风格。推广戏曲艺术并不只有直接把传统戏或新编戏送到国外演出这一种方式,不仅要传递技术手段,更要从舞台艺术升华到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主动地、有意识地展示戏曲文化的精华,从舞台艺术升华到文化传递,让京剧的神韵得以传播。
(五)京剧发展到新阶段的新使命
京剧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越了呀呀学语,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依靠其他艺术乳汁养育的阶段。京剧从少年走向壮年,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担当起像当年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一般,用自己法乳去哺育艺苑百家,滋养其他戏曲,乃至其他艺术形式的职能。
一方面,她依然胸襟开阔,广采博纳,展示了作为一种发展到极为成熟阶段的艺术形式的“汉唐风范”;更重要的是,她以巨大的延展和开拓能力,将自己的影响力播撒到各个艺术之中,既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和完整,又有足够的生命力让受其渗透和干预的艺术呈现出带有京剧独特色彩和韵味的风格,不仅让京剧元素在新的领域发挥功能,而且让很多艺术背后隐隐能看到京剧的背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师法京剧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充实了自己。这是京剧的“魂”附在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体”上,京剧精神也在别的艺术形式上获得另一种意义的新生,这是京剧在文化领域的新贡献和文化史上的新使命。
这种融合是京剧在她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具备了相当的艺术内涵后才能达到的感化、触动力,是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深受追随和仿效的境地,一如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唐诗宋词的余韵,西方的流行音乐中散发着古典音乐的余香,正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吸收和表现了京剧元素的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艺术形式上闪现的有时虽然只是京剧的一点灵光,但映照出的是京剧博大而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在现代艺术的体制中透出了古典的气息,在西方艺术的面纱下露出了东方的微笑。也许随着京剧这种艺术形式生命历程的继续发展,以这种形式呈现的京剧精神会显示出越来越醒目的光彩,这也可能会成为京剧本身越来越普遍的存在方式和展示途径。或许到了某一天,我们不仅能看到原汁原味的京剧,还能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他们受到京剧哺育的基因。这样,京剧就会精神不灭,获得永生。